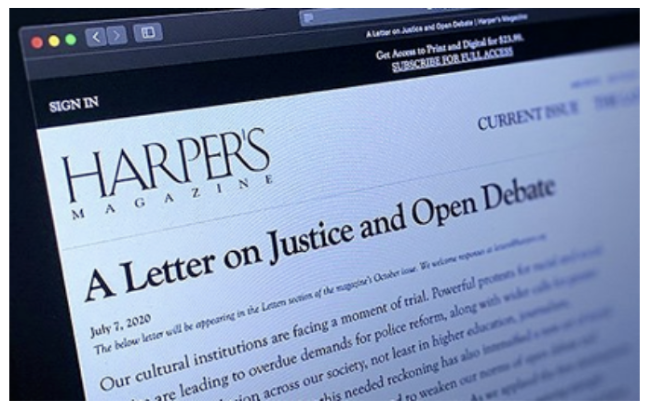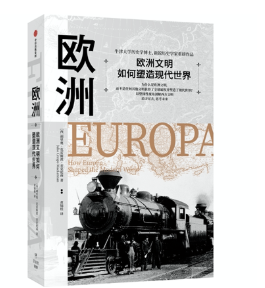这些欧洲知识分子为何反对\"政治正确\"?
经过“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Metoo”运动的洗礼,西方的“政治正确”越来越牢固。在此其间,一场推倒历史人物雕像的运动更是将这种政治狂热付诸行动。首先遭殃的是哥伦布以及美国同盟军将领的雕像。很快,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雕像也被移除。这场运动还蔓延到欧洲:丘吉尔雕像被示威者涂鸦、大英博物馆移走了其创馆收藏家斯隆的雕像……这些历史人物之所以遭殃,其原因不外乎他们生前都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
丘吉尔雕像被涂鸦 推倒雕像运动还衍生出下架影视运动,《乱世佳人》就曾被短暂下架。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推倒雕像和下架影视对于反对种族不公来说有多少实际用处呢?在公共领域抹除有争议的历史记忆能切实地推动社会进步吗?这场运动的激进性使得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泛进步派内部也分裂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 欧洲史学者胡里奥·麦克伦南正是反“政治正确”阵营中的一位代表。在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谈中,麦克伦南表示,欧美流行的“政治正确”是一种新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一系列狂热运动也暴露出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弊病,而这些弊病在欧洲过去500年辉煌的历史中可以找到诸多端倪。 作为欧洲史研究专家,麦克伦南也谈及了自己对欧洲的看法。近些年来,移民问题和恐袭的不断上演已经证明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实验的失败。但他认为存在着一种替代方案,依旧看好欧洲共同体的未来。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建构一套能容纳和囊括全体欧洲人的宏大叙事,构筑一个属于全体欧洲人的“欧洲梦”。 从推倒雕像运动到影视剧下架,欧美“政治正确”的层层攻势也在撕裂着西方泛进步派的知识分子阵营。今年7月,乔姆斯基、福山、J.K.罗琳等知识分子在《哈泼斯》杂志上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了过度“政治正确”的弊端。他们认为,当下的抗议活动已经出现了极端化的现象,保护社会多样性的“政治正确”被狂热的抗议者用来挟持言论自由。一旦这种“封杀文化”失去控制,“政治正确”就会成为一种新的审查制度。 但很快,《The Objective》就发布了一封“反《哈泼斯》”的公开信,这封信跟“《哈泼斯》公开信”针锋相对,指责这些知识精英们根本不理解民众所受的不公。这呈现出当下西方泛进步派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的状况。
《哈泼斯》杂志公开信页面 不管是支持“政治正确”的阵营还是反对“政治正确”的阵营,其实他们都赞同消灭社会的结构性不公,积极推动社会平等进步,认同启蒙的价值观。只不过,反对“政治正确”的阵营认为,“政治正确”是一种激进而民粹的运动,其本质是排他性和专制性的道德审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拿大布兰奇中心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桑坦德学者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即是这一阵营的代表。 麦克伦南认为,倘若对西方历史进行全面的“政治正确”审查,西方近代史上几乎就不存在完全清白历史人物。若某个历史人物因为有道德瑕疵就“一棒子打死”,大家就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约翰·洛克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也是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股东,参与投资奴隶贸易,并且为奴隶制辩护。若只套用当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洛克,洛克就是十恶不赦的种族主义者。但我们却不可否认,洛克的思想也塑造了当今的西方世界。 在这场清算历史的运动中,麦克伦南呼吁,西方人在理解历史时,要尊重当时历史情境和历史局限性。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只要是民粹的历史清算运动都是不可取的。实际上,西方知识精英们对于历史的这种态度,在三年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会呼吁建立一个不以学习柏拉图和康德等白人哲学家为主的课程体系时就显现了出来。 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和知识精英大多批评了这场运动,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认为这些学生很“无知”,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安东尼·塞尔登则认为“政治正确要有失控的危险”,亚非学院宗教与哲学系的主任艾瑞卡·亨特认为学生会的观点“非常滑稽”,有些媒体甚至称这些学生为“PC Snowflake”(追求政治正确的温室花朵)。
被涂鸦的大卫·休谟像。大卫·休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但他曾在著作中表达过对黑人的偏见。因此,爱丁堡大学将大卫·休谟法学院大楼改名为乔治40号广场。 随着近几年“政治正确”运动愈演愈烈,如何面对西方历史黑暗面的问题再次摆上台面。支持“政治正确”的民众和对“政治正确”的激进性持保留意见的知识精英之间的鸿沟也逐步加深。不过,传媒倾向于报道“政治正确”运动的战果,较少关注有着保留意见的知识精英。直到“《哈泼斯》公开信”事件后,许多人才猛然发现泛进步派内部的冲突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也不妨听听这批不赞同“政治正确”知识分子的声音。 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或许能理解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如何认识历史意味着如何建构未来。若完全采纳相对主义的认识论,这虽然能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但也有滑入虚无主义的危险——西方人是什么?西方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或许会“成为问题”。支持《哈泼斯》公开信的知识分子就是认为这场运动触犯到他们所信仰的西方价值观。如何反思殖民的历史遗产、推动社会进步和包容平等,又不至于消解自身呢?如何走“中间路线”成了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 对于麦克伦南——这位坚定而乐观的亲欧派来说,在欧洲建构“欧洲人”的认同是他所推崇的解决方案。如何认知欧洲历史以及欧洲价值观,对如何建构欧洲文明主体性非常重要,这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民粹主义四起,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回潮的年代里,“欧洲人”认同备受冲击。麦克伦南认为,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了,一种崭新的认同模式正在建立当中。这种认同模式是怎么样的?到底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来才能维系“欧洲人”的认同? 为此,麦克伦南写了《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关于欧洲霸权时代和欧洲帝国的著述有很多,但是,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重要影响的作品却不多见,因为对欧洲帝国感兴趣的学者们,大多从国家的角度而不是全欧洲文明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的。麦克伦南希望从欧洲整体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欧洲为现代世界所带来的历史遗产,以重新建构新“欧洲人”身份认同,并以此思考未来欧盟该在新世纪的国际格局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话 胡里奥·麦克伦南
胡里奥·麦克伦南,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拿大布兰奇中心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桑坦德学者,著有《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1 “用政治正确的标准来看, 历史上没有谁是纯粹干净的‘好人’” 新京报: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美国发生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该运动也蔓延到了欧洲。许多地方决定推翻一些种族主义者的雕像,比如大英博物馆移走创馆收藏家斯隆的半身雕像、丘吉尔雕像被示威者涂鸦、利奥波德二世国王雕像被示威者涂漆等。你怎么看待这些行为? 胡里奥·麦克伦南(下文称麦克伦南):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场运动中,推倒雕像是一种蓄意破坏、无知和盲从的表现。比起这种行为,更令我担心的是,有些政府和机构居然屈服于荒谬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一种新的审查制度。如果我们任由“政治正确”泛滥开来,我们许多街道的名字都要被换掉,许多历史雕像都要被推倒。因为,用“政治正确”的标准来看,从亚里士多德到甘地,可能谁也不是纯粹干净的“好人”。许多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筑,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的许多大教堂,都是由奴隶的血汗所建造的。不知道这些建筑需不需要推倒?
BBC有关烦反种族主义者号召移除莱切斯特的一尊“圣雄”甘地雕像的报道。其理由是甘地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性侵犯者。甘地在南非做律师时期,曾认为印度人比黑人高贵,多次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蔑称称呼黑人,并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另一方面,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也不新鲜。许多宗教狂热的政治派别都会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强加给他人,并想消灭掉他们并不喜欢的人以及象征物。假如我们只从二十一世纪的道德标准出发来看历史,我们将永远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在当时历史所处的语境里,欧洲帝国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和坏事。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每个欧洲帝国在扩张中都深信自己是欧洲文明的最好代表,扩张得越大对全人类的益处就越大。现代的美国也相似。如今,有数不清的著作批判当时欧洲殖民者的这种傲慢和罪恶,欧洲的殖民史也成为了当代欧洲的历史包袱。“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者就在掀起一股去殖民化的运动。你怎么看待欧洲的殖民史?你认为今天的欧洲该如何处理殖民史的遗产? 麦克伦南:的确,当时欧洲帝国的殖民者们深信他们文明的优越性,并觉得他们文明的扩张有益于人类的全体利益。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弗逊也深信只有扩张他们的体系和文化,才可能产生“自由帝国”。在客观上,欧洲的殖民主义有其历史意义,但是跟历史上的其他现象一样,殖民主义必然有其弊端。 首先,我个人对殖民主义的理解非常多元。我认为,殖民不仅是一种欧洲现象——在欧洲文明崛起之前,古代大部分文明都会征服甚至掠夺其附近的族群,并通过拓荒开垦移民来扩大其文明的生存疆域。当然,欧洲殖民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是最大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曾被欧洲帝国殖民过,或成为过欧洲国家的保护国。 我们必须要把殖民主义放在具体的时代里进行分析。如今,主流观点会把殖民主义看成完全负面的,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或许会令大家忽视一些史实。奴隶贸易这种邪恶行径伴随着欧洲殖民运动而发展壮大。但是,在欧洲的废奴运动后,非洲也禁止了奴隶贸易——实际上非洲的奴隶贸易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很久了。这也是欧洲影响世界的一个方面。 在十九世纪,许多对欧洲文明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如马克思,他在否定殖民主义的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客观的正面性。因为殖民运动让欧洲社会的许多进步观念、生存方式和制度传播得更快。当然,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带来了极深的灾难。不可否认,直到今天,许多欧洲帝国的前殖民地还在因此挣扎。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西]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著,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版 2 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验或已失败, 另一种替代方案正在诞生 新京报:如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呼吁一个主权更强大的欧盟。他们认为,当下的欧盟并没有很好地让公民参与进来,形成欧洲人的认同感。在财政方面,欧盟也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制定。你怎么看待这些欧盟所存在的问题?你觉得欧盟的哪些问题比较急迫和重要? 麦克伦南:欧元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欧盟形成了货币联盟,但欧盟没有形成财政联盟。这个问题也许会在接下来几年里被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拥有单一货币经济体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整合欧洲身份的核心要务在于整合欧洲、国家和地区这三重身份。每一次危机来临时,欧盟都会成为民众的替罪羊。因为危机加强了各国民众对其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认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塑造出欧洲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在几十年前并不存在。这是欧洲各国人民互动增多的结果。如今,欧盟最急迫的问题是,到底如何建构一套能容纳和囊括全体欧洲人的宏大叙事,即“欧洲梦”。这需要一个宏伟的目标。我相信,欧盟会为其“欧洲梦”而努力成长。 新京报:福利国家作为欧洲国家的重要特征,也是“欧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严重依赖高水平支出的福利制度或许难以为继。你认为在“欧洲梦”里,福利国家该如何可持续发展下去? 麦克伦南:福利国家是“欧洲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福利国家让欧盟在世界上获得了很大影响力——许多国家都想模仿欧洲国家以建立福利国家制度。 尽管金融危机严重伤害了福利国家,但我并不认为福利国家是不可持续的。在管理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上,北欧国家就比南欧国家做得更好。为了阻止之前出现过的债务危机,就需要形成财政联盟。通过有效的改革,福利国家是能被管理好的。当然,这或许意味着有一些免费服务将会收少许费用。不管怎么说,福利国家依然是欧洲之所以为欧洲的关键所在。 新京报:难民问题和外来移民是如今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之一。有人说,难民问题证明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实验的失败。欧洲似乎没有办法同化大量移民,不同群族之间的信任感正在降低。移民的涌入也冲击了欧洲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你怎么看待欧洲的难民问题?你觉得欧洲该如何解决移民冲击原有价值观的问题?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验失败了吗?有替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案吗? 麦克伦南:对于一些欧洲国家来说,移民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有着五十年历史的老问题。在“911事件”之后,移民问题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许多攻击欧洲城市的恐怖分子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实验的失败。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替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案也许正在诞生——这种替代方案首先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这套新方案需要新移民尊重欧洲传统。当然,这套新方案也要求所有人都尊重少数族裔。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许多大城市一直都在接纳移民和难民。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的移民,这些大城市才有得以发展的机会。我其实不认为未来欧洲的移民问题会像以前一样严峻。而且,未来全球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也许会给那些想去欧洲的潜在移民,提供了许多追逐梦想的新选项。 新京报:近年来,西方政界如英国脱欧、川普上台等 “黑天鹅事件”频发。历史并没有如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了。右翼民粹主义开始甚嚣尘上。这也似乎使欧盟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欧盟内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越来越大,疑欧派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你怎么看待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潮?你对欧盟的未来乐观吗? 麦克伦南:在上个十年中,不仅是西方世界,整个世界都在历史的湍流中颠簸航行。我们必须清楚,整个世界刚刚经历过七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广为流传的愤怒情绪,都是民众对这次危机的反应。欧盟要应对英国脱欧和疑欧派所带来的挑战;美国要应对“川普现象”;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正在严重威胁其民主制度。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无处不在。
英国脱欧的示威 其实欧盟早已习惯于解决其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毕竟,欧盟的诞生就建立在对民族主义之恶的深刻反思之上。但是,通过社交媒体而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却是一个新现象。疑欧派和英国例外论能否持续发酵,我们还需要时间观察,不过,现在除了英国并没有其他欧盟成员国真的想退出欧盟。欧盟必须要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英国脱欧是一次自我改革的历史性机会——欧盟要建立一个更不官僚化和更有活力的体系。历史上,欧盟总会在每次大危机后取得新的进步,因此,我对欧盟的未来非常乐观。 3 “如今的国际格局, 让我想起了欧洲的十九世纪” 新京报:在书里,你说在川普当政下的美国,严重违背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杰斐逊原则和威尔逊原则。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关系似乎出现了裂缝。你如何看待美欧关系的未来? 麦克伦南: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基于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原则。他们都共同相信一些值得被守护的价值观。对于美国来说,在许多个世纪里,欧洲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欧洲一直是美国的精神源泉。欧洲和美国是西方世界两根重要的支柱。若美国不与欧洲合作,西方世界就会衰落。因此,未来欧洲和美国之间需要合作无间。这当然有赖于大西洋两岸都能同时拥有识时务的领导人。
美欧关系出现了裂缝。 新京报:有人说,当今世界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有几分相似——国际秩序似乎要变成一种零和游戏。你如何看待这个论断? 麦克伦南:从“9·11事件”开始,我们的世界格局就失调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霸权,每个大国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的确有点像欧洲的十九世纪,这个帝国时代最后以一战作为高潮而结束。 尽管今天的世界跟十九世纪有很多相似之处,幸运的是,我们如今拥有跨国合作组织和全人类共同体的观念。我们现在拥有许多国际组织来协调并监督全球事务的运行。而且,我们已经产生了“全球文明”。许多国家也变得更加成熟——大家不会采取一些不计后果的手段,或者为政治目的而盲目开战。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二十一世纪不一定会爆发公开的战争,但是世界秩序很容易蜕变成激烈的竞争模式。欧盟是当今最能遏止世界秩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呢?欧盟在当今世界秩序里应该扮演哪种角色? 麦克伦南:因为欧洲不像许多地区——欧洲是一个已经“满足了”的文明。欧盟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对全球施加直接影响,更不想将自己的价值观直接强加于别的文明之上。欧盟希望做一些对自己和全世界都更有益的事:确保“全球文明”中的进步理念能够继续流行。因此,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如全球变暖、国际恐怖主义、贫困问题——欧盟对此做得更有决心。 比起其他国家和地区,欧洲也是一个能让大家马上联想起战争的邪恶和大国间不计后果对抗的最佳地区。此外,欧盟还有许多软实力。欧盟的成立意味着许多国际对抗能被超国家组织里的多边合作所解决——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革命的时代到欧盟诞生,欧洲在历史上诞生了最有助于释放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潜力的地方。我相信,欧洲在未来的世界秩序里会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也让原本互相联系相当紧密的世界突然按下暂停键。你是怎么看待新冠肺炎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这场疫情将会如何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 麦克伦南: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全球事务和全球化的方式。一个比以前拥有着更低流动性、更多监控和更少接触的新世界已经出现了。若没有欧盟,许多欧洲国家会更难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这场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危机。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重新定义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机会。黑死病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文艺复兴的诞生。所以我希望在疫情后,这个世界也会有所进步。 | ||
本站刊登日期: 2020-10-13 11:07:00
-
 召开全球民主峰会,拜登吹响捍卫民主的集结号
召开全球民主峰会,拜登吹响捍卫民主的集结号
-
 表意文字不利于抽象思维
表意文字不利于抽象思维
-
 相比清洗吉伦特派的暴民政治,“冲击国会山”只是一场赝品政变
相比清洗吉伦特派的暴民政治,“冲击国会山”只是一场赝品政变
-
 决定2021年病毒大战胜负的秘诀和展望
决定2021年病毒大战胜负的秘诀和展望
-
 美國警察是種族主義者嗎?
美國警察是種族主義者嗎?
-
 人活一辈子,脊梁要挺直
人活一辈子,脊梁要挺直
-
 中华派、西化派和北化派
中华派、西化派和北化派
-
 这些欧洲知识分子为何反对\"政治正确\"?
这些欧洲知识分子为何反对\"政治正确\"?
-
 特朗普生病信息公开 威权国家领导人生病为何是秘密?
特朗普生病信息公开 威权国家领导人生病为何是秘密?
-
 “阴谋论”调可休矣,宪法危机有可能?中共党员禁移民 (视频)
“阴谋论”调可休矣,宪法危机有可能?中共党员禁移民 (视频)
-
 种族主义、民权运动与BLM
种族主义、民权运动与BLM
-
 中国百年灾难史最核心的乱源
中国百年灾难史最核心的乱源
-
 预测南海大战的关键因素
预测南海大战的关键因素
-
 “程序性正义”与“纠偏行动”
“程序性正义”与“纠偏行动”
-
 命运底色
命运底色
-
 被中国官媒引用的哈佛教授:从未怀疑新冠病毒起源武汉
被中国官媒引用的哈佛教授:从未怀疑新冠病毒起源武汉
-
 全球疫期中的生活隨感之九、十
全球疫期中的生活隨感之九、十
-
 全球疫期中的生活隨感之七、八
全球疫期中的生活隨感之七、八